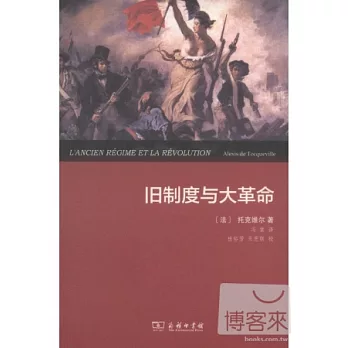
舊制度與大革命,作者托克維爾。 是了解法國大革命的經典著作。 網路下載:電子書。看過整本書後,我簡單敘述我所吸收認知的架構,後續針對我感受深刻的章節,我會引用內文說明。
壹、法國大革命是由許多因素造成,而這些因素追溯根本,大多來自於王權的礦張,中央集權導致的。在14世紀,封建制度下,領主跟土地、領地下的人民,有治理、照顧、收稅...等權利義務,一個領地就跟一個小王國差不多,地方自治是主要架構,封建領地中有自己的議會,領地內的貴族、教室、平民各階層有代表討論公共政策的機制,地方領主享有特權跟治理權的時候,也負擔起義務。 在封建制度下的地方可以跟國王形成制衡對抗,而非單純地聽命行事。
王權的擴張,貴族跟國王做了一筆魔鬼交易,國王讓貴族享有特權與免稅權,換取貴族放棄治權,對貴族來說,免去義務,只享受特權,實在太誘人了,但他們不知道,他們也失去跟人民之間的關係,把自己跟人民剝離。這筆交易讓國王得以跳過貴族,把治理權加在人民身上,可以直接對人民徵稅、要求服勞役,除此之外,國王給貴族的好處,也一併加到人民身上,人民負擔變得無比沉重。這樣的做法,導致了以下幾件事情
1. 貴族跟人民之間關係改變。以往貴族跟人民相互權利義務,貴族要救濟貧苦、賑災、要聽取民意、要做司法判決、要收稅,跟人民之間形成一個體系,但現在貴族只剩特權,沒有義務了,人民成了單純金錢的來源,對於貴族來說,平民只是個陌生人,那就盡可能地榨取。此外,既然跟這邊人民也沒關係了,貴族就開始遠離農村,聚集到巴黎去,拿著錢到巴黎享受去了。貴族隨著時間漸漸地凝固成一個類似種姓的階級,跟底層、新興資產階級完全分隔開,雙方不通婚、往來有著無法逾越的界線。
2. 大革命常提到的教士,我們可以把教士當作貴族,只是他們比貴族還多擁有農奴、十一稅的徵收權。 當時的法國正教沒有分立,教士可以擔任政府的官職,享受更多的特權。也因為宗教跟世俗綁定太深,以至於革除特權之時,宗教也成了打倒的對象。但宗教卻是人的基本需求,大革命後沒多久,宗教又植入人心了。
3. 新興資產階級。法國隨著工業化,科技進步,出現一群上升的階級,新興的資產階級有錢,他們透過買官取得特權,透過學習提升自己。這權人活得越來越像貴族,甚至跟貴族已經沒有差異了。但這些人也往巴黎跑,農村中但有點錢的人,有點能力的人,都在想辦法到城市買官,到巴黎享受生活,把農村變成產生現金流的資產,跟貴族一樣不關心農村的死活。
4. 農村的農民。 最悲慘的一群,貴族的特權、租稅他們要承受,國王額外攤派的稅跟勞役,他們也要承受。他們承受了所有的苛捐雜稅,還要受到不公平的司法對待。最糟的是,任何有一點辦法的人,都會離開農村,去城市買官,想著到巴黎奔前程享福去。留在農村的人,越來越愚昧,越來越對原本的處境感到無力。 只要有一點光明,他們會不顧一切往前衝去,即使踩踏擋在前面的人。
5. 各階層被孤立,每個人都被原子化。各階層還相互痛惡對方,貴族與新興資產階級相互痛恨,農民痛恨貴族、新興階級。 新興階級分為若干小團體,為各自謀私利而相互厭惡。各自對彼此的仇視,對現實的不滿,原子化的個人或是小團體,都會怪罪起中央政府,也同時盼望著中央政府(國王)來解決,
6. 王權不斷地擴大,中央政府也不斷地強大,且深入各地方。中央設立御前會議,會議的組成大多是新興資產階級或是平民,同時在地方建立官僚體制去治理整個法國各個城市與農村,中央權力越來越強大,治理的權力開始深入底層,連農村要修教堂的屋頂都要等御前會議(國王)決定。
國王大多任命新興資產階級、平民為官僚,這個動作對國王是為了好控制,長期下來,卻造成貴族對這些實際治理職務感到是低下的,所以貴族大多不願意擔任官僚。貴族是少數具有能量可以對抗國王了,現在他們連這點力量都不願意去保留了。
王權為了不受干預,開始繞開司法,設立行政法院,凡是涉及到政府、政府官員或是國王覺得不適合一般法院的案件,都要到行政法院來處理,或者是御前會議處理。
7.法院法官。 法官原則上都還能保持獨立性,但是王權開始破壞它或是繞開他,一如上述提到的,一個案件歸不歸法院管轄,那要看國王怎麼說。 此外,因為習慣法的關係,法院需要先例、需要依循的法規,所以與時俱進的能力相對比較差。 現在行政權不僅限制司法、刻意繞開司法,行政權還因為有彈性面對新的改變,讓自己管轄範圍與時俱進地擴大,變相壓縮司法管轄範圍,法院的力量也越來越小了。
8. 巴黎因為中央集權,累積大量的資源,逐漸成為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全法國都看著巴黎,巴黎怎麼動作,大家就跟著做。所以當巴士底監獄被攻陷的時候,整個革命之火才會快速燒往整個法國。
9.文學家、哲學家領導大革命。 這是讓大革命瘋狂的原因。 國王對這些人談論政治、社會原理都很開放,貴族也對他們的哲學、思想、文學表達支持與喜好。他們的言論更是能夠深入一般困苦的農民心裡,但這些人有空談理論,卻沒有實際政治經驗跟務實的執行能力。大革命爆發後,他們領導著革命,也把革命帶向野蠻、混亂。
引述原文:
研究法國革命史的人應該清楚,大革命的指導思想恰巧是和那些卷帙浩繁的評論治國的抽象著作是一樣的:即本著對一般理論,對完備的立法體系和精確對稱的法律的相同愛好;對現存事物的同等蔑視;對理論的同樣信任;對於政治機構中獨特、精巧、新穎的東西的同一興致; 遵照邏輯法則,依據統一方案,一舉徹底改革結構,而不在枝節上修修 補補。這是何等令人感到害怕的景象!
因為有些東西在作家身上表現出來的會是美好的,可是如果移植到政治家身上,可能就會變成災難性的後果,那些帶來美好著作的事物,卻很可能導致一場浩大的革命
10. 上述因為王權的礦張,造成上述林林總總的不平與痛苦,整個社會就像酷熱天氣下的乾柴。 這時候,文學家還跑來贊助火藥桶,跟澆上汽油。 而上位者、特權者不僅不知道危險,他們還在一旁玩起噴火特技,完全不擔心火藥桶會爆炸。
這個噴火特技就是讓人厭惡的點評,這些上位者會說出政策的種種不公平,說出農民的痛苦,誥文中充滿了憐憫與高高在上的感覺。對於那邊水深火熱的人來說,原來上位者都知道啊 ! 就像強姦犯跑來跟受害者說:『別放心上,事情都過去了, 我以後會改的。』 我無法想像上位者的白目,但我可以理解平民的痛苦跟賭爛。 但即使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可憐的平民還是選擇再忍一下。
就在平民無止盡的忍耐下,我們上位者決定再把他們白目的境界更上一層樓。那堆柴火排列的不太好看,且讓我拿起火把去絞拌均勻一些。
引述原文:
政府的結構尚未改變,但之前政府那些限定個人地位和政府事務的 附屬法律卻已經被廢除或修改。 行業理事會被破壞,接著又恢復了一部分,這種變化深刻地改變了 工人和僱主的舊關係。這些關係不僅和以前不一樣,而且變得不那麼確 定和友善。有關禮拜日的規定遭到破壞,國家的監管尚沒有穩固建立。
工匠夾在政府與老闆之間,處於一種比較尷尬的地位,不知道這二者中 誰能容納和保護他。不僅僅是工匠,其實整個城市的下層階級突然間就 陷入了這種茫然的無政府狀態。一旦他們重新回到政治舞臺上,那麼這 種形勢可能就會產生嚴重的後果。
在大革命爆發的前一年,國王的詔書給司法領域的所有各部門造成 了混亂。無數新的法庭設立,而其他法庭又大批地被廢除,一切有關管 轄權的規定都被改變。
然而在法國,一如我之前在別的地方所說的,負責審判和執行判決的人員數量極其龐大,可以這麼說,幾乎整個資產階 級都與法庭產生了或親或疏的關係。新法律的實施打亂了千家萬戶的處境和財產,讓他們的地位也變得不那麼可靠。國王的詔書也給申訴人帶 來麻煩,因為在這場司法革命中,他們很難找到可以進行審判的法庭和 可以應用的法律。
最後,火藥桶終於爆炸了。 大革命爆發了,幾乎所有人都蒙在鼓裡,也沒人知道這場革命將怎麼發展。一場打倒所有舊制度的革命開始了。
貳、最後大革命的成果是甚麼? 我建議大家去看這本書的前言,成果並不如我們想像的或是教科書所說。
引述原文:
1789年,法國人民通過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努力,將自身的命運切成 兩斷,用一道鴻溝隔開了過去和未來。他們表現得謹小慎微,生怕過去 的舊事物會影響到他們的新世界:於是,他們給自己設定了各種條條框 框,想盡一切辦法要把自己塑造成不同於父輩的新生代。
我一直認為,在這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中,法國人所取得的成就並 不如外界所想象的那麼大,也沒有達到他們自己最初的既定目標。我深深相信,法國人幾乎不由自主地繼承了舊制度的一切,包括大部分的感 情、習慣以及思想,甚至可以說,他們正是憑藉著這些東西領導了這場摧毀舊制度的大革命。
引述原文:
離1789年越近,我越能清晰地看到引發大革命的那種 精神是如何誕生以及發展壯大的。法國大革命的整個面貌逐漸在我眼前 展現,它已呈現出了自己的性格和特點,而這就是它本身。我不但從這 裡發現了革命的肇始原因,我甚至進一步發現了它長期目標的預兆。
大革命可分為兩個截然不同的階段,在第一個階段,法國人貌似要摧毀過 去的一切,而在第二階段,他們卻要恢復一部分已被摒棄的事物。1789 年,舊制度中有很多法律條文和政治習慣突然消失,而在幾年後,它們 又再次出現,就像那些已經沉沒於地下的河流,在不遠處重新冒出,讓人們在新的河岸看到同一條河流。
我會對這場大革命的程序進行簡要的追溯,與此同時,我會努力說 明:這些法國人因為哪些事件和錯誤的決策而最終拋棄了他們的初衷, 忘記了自由的意義,而只想成為世界征服者的平等奴僕;法國人民在推 翻舊的專制政府後,是如何被一個更為強大和專制的政府奪取了全部權 力,讓以高昂代價換來的自由成為泡影,只留下空無一物的自由假象;
這個專制政府如何將普選權標榜為人民主權,而事實上,選舉人既不瞭 解內情,無法進行商議,又沒有實權,不能進行選擇;它如何施壓,迫 使議會屈服和沉默,並把這吹噓為表決捐稅權;此外,該專制政府還取 締了國民自治權和權利的各種主要保障,取消了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以 及寫作自由,而這些正是1789年法國大革命所取得的最寶貴成果,最為 過分的是,它竟然還以這個偉大的名義自我標榜。
参、以下是書中的節錄,建議大家可以去看書,我覺得寫得太深刻,太有感了。
一、關於中央集權。
引述原文:
中央政府並不侷限於在農民貧困的時候賑濟他們,還要教給他們致 富方法,幫助他們,甚至在必要的時候促使他們去致富。為此,中央政 府通過總督及其代理,經常散發印有農耕技術的小冊子,設立農業協 會,承諾紅利,花費巨資建立苗圃,並將所產種苗分發給農民。如果中 央政府在當時減輕壓在農業勞動上的重擔,縮小各種不平等差距,效果 也許會更好,但是,顯然這一點從沒人想到過。
御前會議有時會試圖促使個人發家致富,無論他是否有這種意願。 有很多法令迫使手工業者使用某種方法生產特定產品,由於總督不可能 監督所有這些法令的貫徹實施,便出現了工業巡視員,他們來往於各省 之間進行監控。 御前會議有時會發布禁令,禁止在它認為不適宜種植某種作物的土 地上種植這種作物。甚至有禁令要求人們拔掉在它認為貧瘠的土壤上種 植的葡萄,可見政府的角色已經由統治者轉變為監護人。
引述原文:
總督費盡心思,不斷擴大這種特別的司法許可權,他們提醒財政大 臣,讓其縱容御前會議。值得一提的是,有一個官員曾這樣提出調案的 理由:「雖然普通法官要遵從現有法規,懲罰違法行為,不過御前會議 永遠都可以有例外。」 據此,總督和御前會議常常親自審理一些與政府沒有明顯關聯或完 全無關的議案。曾經有個貴族與鄰居發生爭執,對法官的判決不服,要 求御前會議調案重審,監察官對此案的答覆是:「儘管這個案件只是個 普通法庭可以審理的民事問題,但如果國王陛下願意,他就可以直接審 理一切案件,而不需要任何理由。」
引述原文:
舊制度下的普通法庭如果想對中央政府任何一名官員起訴,必須先 考慮御前會議的一道裁決:被告不受普通法庭法官審理,應轉由御前會 議授權的專員審理;因為,就像那時一位行政法院官員所描述的,受到 這種攻擊的官員會給普通法官留下不良印象,甚至殃及王權。這類調案 几乎天天都有,不僅有政府要員,還會涉及一些小官吏。
只要與政府沾 上一點關係,便可以在政府之外的地方胡作非為。一個農民控訴虐待他 的橋樑公路工程局負責調配徭役的監工。御前會議宣佈接手此案,總工 程師在私下寫給總督的信件中這樣說道:「的確,該監工應受到懲處, 但卻不能任由事態這樣發展,對於公路橋樑工程局來講,最關鍵的是讓 普通法庭不聽取也不受理役工對監工的控訴。開了這個先例,公眾出於 對這些官員的仇恨,就會不斷提出新的訴訟,這將影響到工程進展。」
還有一種情況,一個政府承包商拿了鄰近地域的建築材料,總督親 自向財政大臣報告:「我無法向您說得更明白,讓政府承包商接受普通 法庭審理,這將極大地危害政府利益,因為普通法庭和政府的原則從來 都是相沖突的。」 這幾行差不多是整整一個世紀前寫的文字,可是寫這些的官員和我 們同時代的人多麼相像啊!
引述原文:
儘管18世紀的報紙,或當時人們所說的公報,刊載的四行詩比辯論 文章還多,但是政府妒忌的目光已經投向了這支微弱的力量。政府對書 籍很寬鬆,對報紙卻很嚴苛;因為無法蠻橫地直接取締,就努力將報刊 收歸官用。我發現了一份1761年發給各總督的通告,其中國王(即路易 十五)決定,從現在開始,政府將監督《法蘭西報》的編排,通告說: 「鑑於國王陛下想讓這份報紙更有趣味,確保它比其它的報刊更好,所 以,你們需要寄一份簡訊給我,記下你們行政區內激發民眾好奇心的一 切事物,尤其是關於自然科學和歷史的奇聞趣事。」通告還附有一份簡介,其中聲稱,新報紙會比之前的出版週期要短,內容更豐富,但訂閱 費用會便宜很多。
總督收到這些檔案後,就寫信下令其代理貫徹執行,但是,總督代 理最開始的答覆是他們毫不知情。於是大臣發出了第二封信,斥責外省 效率低下。「國王陛下命令我通知你們,他要你們嚴肅認真地負責此 事,向你們的下級官員下達最明確的指令。」
總督代理開始行動起來: 有人報告說有個走私鹽的罪犯被處絞刑而且展現出極大的勇氣;還有人 報告其行政區有個女人一胎生三個女孩;第三位報告突發一場恐怖的暴 風雨,卻沒有任何損失;還有人宣稱,雖然他特別留意了,但一件有價 值的事也沒有發現,不過他自己訂閱了這份有用的報紙,並打算告訴更 多有學識的人都訂閱。然而這些努力並沒有帶來多大效果,有位大臣在 另一封信中這樣說道:「國王不辭辛苦,親自釐清各項措施,幫助報紙 辦得更好,並願意賦予這家報紙應得的榮譽和名聲,但國王對他的旨意這樣不受重視表示非常不滿。」
所以歷史就像一座畫廊,原作很少,更多的是複製品。
引述原文:
這些思想絕不止出現在書本上,它們還深入到所有人的精神世界 裡,與習慣融合在一起,成為人們習俗的一部分,並進入到實際日常生 活中的各個關節。大家普遍認為,只有國家的介入,一些重要事務才能 搞得好。 一般農民對條條框框的法規反抗最凶,但連他們都相信,如果農業 沒有什麼進展,主要責任在政府,因為政府沒有給他們提供足夠的諮詢 和幫助。
一個農民寫信給總督,其悲憤的態度,已昭示著大革命的來 臨:「為什麼政府不派遣巡視員,每年巡視一遍各省的農作物狀況,教 育莊稼人改良耕作方法,告訴他們如何餵養牲畜、如何出售以及到哪裡 出售農產品?這些巡視員應該得到豐厚的回報,而最出色的耕種者應得 到榮譽獎勵。」十字勳章和巡視員!這套方法是薩福克郡的農夫怎麼也 想不出來的!
在多數人看來,現在只有政府才能保障公共秩序:民眾只怕騎警 隊,而領主們只相信騎警隊。對他們來說,騎警隊的騎兵不僅是秩序的 重要捍衛者,甚至就是秩序本身。吉耶納省議會曾提過:「那些什麼也 不怕的人,只要一看到騎警隊就自覺收斂起來,這是公認的事實。」所 以大家都希望有騎兵站在門口。這一類請求在總督轄區的檔案中隨處可 見,好像沒人想到藏在騎兵後面的極可能就是主人。
看到本世紀(19世紀)初中央集權制如此簡單地在法國得以重建, 我們不必感到絲毫驚訝。1789年的革命者曾推倒這座建築,但是它的根 基卻印在這些推倒者的心中,因此,在此基礎上,它才能突然間再次崛 起,甚至比以往更為堅固。
引述原文:
1740年孟德斯鳩[7]曾給他的一位朋友寫信說:「在法國,只有巴黎 以及離巴黎遙遠的外省,因為巴黎還沒時間將它們一一吞噬。」1750 年,那位充滿奇異幻想但有時不乏深刻見解的米拉波侯爵不指名地談及 巴黎,
他說:「首都對於一個國家來說是必要的,但是,如果頭腦長得 過大,身體就容易因患上中風而癱瘓。如果外省處於一種直接依附的地 位,其居民被看作二等公民,如果不給他們任何在本地獲取功名利祿的 職業和晉升機會,而致使一切有才能的人都湧向首都的話,其後果將會 如何?」米拉波侯爵把這種情況稱為一種無聲的革命,這種革命從外省 帶走了領導者、商人,以及通常意義上的「知識分子」。
但是他們的民情是 激動的,可以說一觸即發,只是尚未採取行動而已。每到一座城市,阿 瑟·揚都會詢問當地的居民們下一步如何打算。「 答案差不多都一樣,」他說道,「他們會說,必須看看巴黎怎麼幹 的,我們畢竟只是一個外省城市。」他進一步說道:「除非他們已經確 切得知巴黎在想些什麼,否則這些人甚至都不敢有自己的獨立見解。」
引述原文:
由此可見,對於那些40年來在我們眼前不斷更迭的所有政府來說, 其垮臺的重要原因正是:巴黎的至尊權力和行政上的中央集權制。這幾 乎已成為共識,我無需費力再進行解釋。同時,這個原因也在很大程度 上導致了舊君主制的突然毀滅,它是法國大革命的主因之一,並引起了 此後所有的其他革命
在18世紀末,人們或許尚可分辨出貴族與資產者舉止行為的不同, 因為,被人們稱為「舉止行為」的這種外在形式,比其他任何事物的變 化都需要時間。但事實上,所有高居平民之上的人都彼此相似:他們具 有同樣的思想習慣、嗜好,沉迷於同樣的娛樂、閱讀同一本書甚至講著 同一種言語。
貴族與資產者之間除權利外,沒有任何差別。 我懷疑在其他國家這種現象是否能夠達到同樣的程度,即便是在英 國,不同階級雖然被共同的利益牢固地拴在了一起,但他們在精神與風 尚方面仍會有所不同。政治自由具有一種令人欽佩的力量,這種力量能 夠在所有階級的公民之間建立起必要的、互相依附的聯絡,但這些都不 能使他們彼此相似。恰恰相反,長遠來看,正是那種獨夫體制,才使得 人們彼此相似,卻又對彼此的命運漠不關心。
二、英國有階級流動,而法國階級僵化
引述原文:
英國不是把貴族制度改頭換面,而是將其徹底摧毀。在英國,貴 族與平民從事著同樣的事務,可以選擇同樣的職業,而更為有意義的現 象是貴族與平民之間的通婚。在英國,最大領主的女兒可以嫁給新貴 族,而不會覺得有失體面。 如果你想了解種姓以及它本身創造的各種思想、習慣、障礙在英國 是否已被徹底消除,最好的途徑是考察一下這裡的婚姻狀況。
只有在英 國,你才能發現你從未發現過的帶有決定性的特徵。而在民主已有60年 之久的法國,甚至到了今天,你很難找到這種特徵。新舊家族在所有方 面似乎都沒什麼分別,然而兩者還是極力避免聯姻。 據說,與其他國家的貴族相比,英國貴族一向更為謹慎、靈活、開 放。然而,這種嚴格意義上的貴族在英國早已不存在了,如果貴族這個 詞在此仍具有其他地方保留的古老的嚴密意義的話。
引述原文:
幾百年以來,在英國,所有的賦稅不 平等都已經消失,但是對貧困階級有利的不平等的納稅政策除外。請想 一下,不一樣的政治原則會將地理上如此相近的兩個民族推向何處!18 世紀的法國富人享有捐稅特權,而英國此項權利卻屬於窮人。
在法國, 貴族因失去統治權,而以獲得終身免稅權作為補償;在英國,貴族為了 進行統治,卻必須承擔最沉重的公共負擔。 在14世紀,「除非徵得納稅人同意,否則不得徵稅」這句話在英法 兩國似乎同樣深入人心。人們常常說到這句話:遵守它就是服從法律, 違反它就是實行暴政。正如我所說的,那時候英法兩國的政治機構多有 相似,不過後來隨著時間的流逝,兩個民族間不同之處越來越多,命運 相互分離。它們彷彿是從鄰近點出發的兩條線,由於傾斜度不同,所以 兩條線越延長,距離越遠。
引述原文:
我們已向人們提供了忘不掉的例證。60年前,導致舊法國分裂的各 個階級在長期被重重障礙隔絕之後,他們重新接觸時,首先碰到的卻是 彼此的傷疤,重聚只不過是為了廝殺。時至今日,雖然他們已經遠離塵 世,但人間還留有他們互相嫉妒和仇視的影子。
三、底層人民的絕望
引述原文:
迪爾格曾說起另一個省的狀況:「收稅員這個職 務讓那些任職者感到絕望,而且往往以破產告終,以這種方式,村裡所 有原本殷實的家庭逐一陷入貧困。」 然而,這些橫徵暴斂的人不只是受害者,他們還兼有暴君的角色。 在他們的任期內,不僅讓自己破產,還掌握著大量破產家庭的命運。
正如省議會所說的那樣:「他們對於自己親屬和朋友的優惠,對於敵人的 仇恨和報復,對於庇護者的需求,唯恐引起那些給他們派活的有錢公民 的不快,這所有的一切都在他內心翻滾,和正義感搏鬥。」恐懼往往讓 收稅人變得殘酷無情,在某些教區裡,如果沒有催稅員和執達員陪同, 收稅員就會寸步難行。1764年,有位總督致信某大臣:「如果收稅員不 帶著執達員一同前往,那麼繳稅者往往會拒絕繳納。」
吉耶內省議會告 知我們:「僅維勒弗朗什財政區一處,就有106個拘役傳令人和其他負 責執達的助理在道路上終日奔波。」 為了避免這種橫徵暴斂,18世紀全盛時期的法國農民竟然也像中世 紀的猶太人一樣,在外表上裝得窮困不堪,實際上卻不是這樣。他為自 己的富裕感到害怕,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我在距吉耶內百里之內的地 方得到了一份檔案,它對此提供了非常明顯的證據。曼恩農業協會在它 1761年的報告中宣稱,它打算以分配牲口的方式對農民進行鼓勵,然 而,這個想法最後沒有施行,因為農業協會認為「人們的嫉妒心會給獲 獎者帶來危險,讓他們在獲獎後的幾年裡因強加的捐稅而煩惱不已。」
引述原文:
1767年,舒瓦瑟爾公爵想要一舉掃除法國的乞討現象。 在這些總督的通訊中,我們可以看到其手段是多麼的殘酷:他們任命騎 警隊前去逮捕王國境內的所有乞丐,當時被捕的乞丐有5萬之多,那些 身強力壯的乞丐被抓去服苦役,其餘的老弱病殘則推給了40多家乞丐收 容所,讓那些有錢人再發發善心。
然而,政府對民眾的壓迫不僅表現在處境的惡化上,還更多地表現 在不允許他們改善自己的處境上。這些人是自由的所有者,他們幾乎和 自己的農奴祖先一樣愚昧,並且更加窮苦。在這個工藝水平突飛猛進的 時代,他們卻不懂技術,在這個知識文化光彩奪目的世界,他們卻還沒 開化。雖然他們身上遺傳有他們種族特有的智慧,卻不知道如何使用 它,甚至他們連種地這一唯一的營生都做不好。有位著名的英國農學家 說道:「我眼前看到的是停留在10世紀的農業。」這些人唯一擅長的只 有從軍打仗,在這個行當裡,他們和其他階級還存在著天生的必要聯 絡。 農民被禁錮在這道窮苦孤立的深淵中,幾乎完全與世隔絕。
引述原文:
假設農民沒有土地,那麼他們就會對封建體制附加在地產上的種種 負擔無動於衷。如果他不租土地,什一稅跟他又有什麼關係?他從租金 收入中扣繳什一稅。如果他沒有自己的土地,地租也跟他沒關係。如果 他只是替別人打工,那麼其間遇到的種種剝削又與他何干?
再者,如果法國農民還是受領主管轄,他們就會覺得封建體制沒有 什麼接受不了的,因為這只是國家體制使然。 當貴族既擁有特權又擁有政權,他們進行統治時,其個人權力就更 大,而且具有隱蔽性。在封建時代,人們看貴族就像是今天我們看政府:為了獲取貴族賦予的權益,就必須接受貴族強加的負擔。貴族享有 令人厭煩的特權,擁有讓人無法忍受的權利;但是貴族保障公共秩序, 維護公正,實施法律,賑濟貧困,處理公共事務。
當貴族不再處理這些 事情,貴族特權的份量就顯得非常沉重了,甚至就連貴族的存在也成了 一個值得質疑的問題。 試想一下18世紀的法國農民,或是現在熟悉的農民,因為法國農民 一點都沒變:他們的地位變了,但性格還是一如既往。看看我引用的材 料裡所描述的農民吧,他熱愛土地,不惜一切代價用畢生積蓄購買土 地。為了得到土地,他得先付錢,不過並不是給政府,而是給鄰近有土 地的莊園主,這些人與他一樣跟政府毫無關係,和他一樣沒有權勢。
當他終於買到一塊土地時,他把心和種子一起種到地裡。在天地間的一個 角落裡,他擁有一塊土地,他對此感到自豪。可是現在這些鄰居把他帶 離他的土地,強迫他無償為他們在別的地方幹活。他想阻止他們糟踐他 的收成,可卻無能為力。
他們等候在河流岔口,向他索取通行稅。他在 市場上又碰到他們,要想賣掉自己生產的糧食必須先向他們交錢。 回到家裡,他打算自己食用剩下的麥子,這些都是他親手播種,親 眼看著長大的,可是他必須到他們的磨坊裡磨面,用他們的烤箱烘麵包。
他必須將那小塊土地上的部分收益當作租金交給他們,而這些租金 是永恆的,且不能贖取的。 不管他做什麼,到處都有這些討厭的人來妨礙他,他們破壞了他的 幸福,干擾他的勞動,掠奪他的農產品;而當他擺脫了他們,卻有另一 幫穿著黑袍的人出現了,奪走了他的絕大部分收穫。不妨設想一下這位 農民的環境、需求、個性以及情感,並計算一下(如果可以計算的 話),農民心中該積攢了多少仇恨和嫉妒。
封建體制已不再是一種政治制度,但它依然是所有公民社會中最大 的一種。範圍變小了,它激發的仇恨卻更大。有句話說得好:摧毀部分 中世紀制度,會讓剩下的那些更加令人厭惡。
其實還有很多,但因為內容實在太多了,都要把整本書都要放進來了,避免篇幅太多,在此,建議大家去看原文。
参、心得:
一、專制制度是最大邪惡。自由是那麼地可貴。
引述原文:
在這種型別的社會中,人們彼此之間不再有種姓、階級、行會以及 家庭的聯絡,人們只關心自己的個人利益,在極為狹隘的個人主義中過 活,公共品德完全窒息。專制制度不僅不會抵抗這種傾向,還會使其大 行其道,它奪去了公民身上所有的共同感情,所有的相互需求,所有友 好相處的必要性,以及所有共同行動的機會。專制制度就像一堵牆,將 人們封閉在各自的私人生活中。人們原本就習慣自私,專制制度又讓他 們彼此孤立;人們原本就彼此冷眼相待,專制制度又讓他們冷若冰霜。
在這樣的社會裡,沒有什麼事物是一成不變的,每一個人都處心積 慮地往上爬,生怕自己地位下滑。金錢成為區分高低貴賤的象徵,由於 金錢具有流動性,所以隨著它不斷地轉手,人們的個人處境、家庭環境 也隨之變化,在這種情形下,每個人都拼了命地賺錢,不擇手段發財致 富的渴望、對商業的依戀、對物質享受的追求,就成了這個社會的普遍 感情。這種感情遍佈在所有的社會成員之中,甚至出現在一向與此無緣 的階級中,如果不想辦法阻止,整個民族都會跟著墮落下去。
然而,專制制度卻火上澆油,從本質上支援這種感情,因為這種讓 人消沉的感情對專制制度非常有利,它將人們的目光從公共事務上移 走,甚至讓他們一想到革命,就渾身顫抖,認為唯有專制制度能夠給它 們提供庇護和生財之道。由此,人們的貪婪日盛,以不道德甚至非法的 手段攫取財物。其實,即便沒有專制制度,這種情感也有可能變得強 烈,而有了專制制度,這種情感就佔據了統領地位。 相反,在這類社會中,唯有自由才能抑制其固有的種種弊端,讓社 會不至於沿著崩潰的斜坡往下滑。
而事實上,只有自由才能讓獨立的公 民擺脫孤立狀態,促使他們彼此靠近;只有自由才能讓人們覺得溫暖, 並且逐漸地聯合起來,因為要處理好公共事務,就必須要互相體諒、換 位思考;只有自由才能讓人們抵制拜金主義,從雞毛蒜皮的日常小事中掙脫出來,並且時刻都感覺到祖國近在咫尺;只有自由才能給予人們以 更高尚的激情,從而取代對世俗幸福的眷戀,讓人們具有比發家致富更 為遠大的目標,並且進行知識文化創造,從而能夠辨別人類的善惡美醜。
缺乏自由的民主社會也許是富裕、華麗甚至是輝煌的,並因其普通 大眾的舉足輕重而顯得強盛,在那裡,我們可以看到具有私人美德的家 庭慈父、誠實的商人以及令人尊敬的企業家,甚至可以看到勇於犧牲的 基督徒,當他們的國家消失於塵世,宗教的最大榮耀,就是在最腐敗的 環境下創造優秀的基督徒,比如,在羅馬帝國最腐朽的時候,就充斥著 很多優秀的基督徒。儘管如此,我還是要說,在這種社會裡,絕對看不 到偉大的公民,我還可以斷言,一旦平等和專制結合,人們心靈和精神 的普遍標準就會不斷地下降。
二、改革要務實地改、慢慢地改。就像英國一樣,在一個框架下,慢慢地替換掉改變。 不要被文人、空泛的理想牽著鼻子走,這些想像中的美好,往往是通往地獄的道路。
引述原文:
這些作家們自身的處境是引導他們關注政府問題的普遍抽 象理論的基石,並對這種普遍理論深信不疑。他們的生活幾乎完全脫離 現實,沒有什麼東西能夠限制他們天性中的那份熱情。對於迫切的改革 會遇到哪些現實障礙,他們也未得到任何事物的預先警告;對於革命會 帶來的那些危險,他們也未曾深思或者說連想也沒想過。由於現實政治 沒有任何自由,以至於他們對政界幾乎毫無所知,並且視而不見。他們 在政界也沒有什麼作為,當然他們也看不到他人的所作所為。
即便是那些不過問國事的人,只要是見過自由社會、聽過其中的爭 論,就能受到教育,而作家們幾乎連這種膚淺的教育也沒有。因為沒有 受到這樣或那樣的束縛和限制,所以作家們敢於大膽創新,更加熱愛那 些普遍意義上的思想和體系,對古代的哲理也就越來越鄙視,也更相信 他們個人的理性。這種現象在那些研究政治學並以此著述的作家中是幾 乎找不到的。
由於思想上的侷限和觀念愚昧,民眾對他們幾乎是言聽計從,並熱 烈擁護。假如法國人能像以前一樣在三級會議中參政,每天都能在省議 會中繼續致力於地方行政,那麼我可以肯定地說,民眾是不會像現在這 樣受到作家們思想的鼓動的。他們會依據一定的規章來維持秩序,以防 止純理論。
假如像英國人一樣,法國人也不至於完全廢除舊的體制,而應該是 學習英國通過政治實踐來逐漸改變政治體制。這樣的話,他們應該也不 會如此迷戀那些作家們臆想出來的新花樣。但是,現實情況是每個法國 人在他的財產、人身、福利或自尊方面無時無刻不受到舊法律、舊政治 慣例、舊權力殘餘的侵擾,而他卻找不到任何方法來解決。擺在他面前 的似乎只有兩條路:要麼全盤忍受,要麼徹底摧毀這個政權。 但相對於其他似有實無的種種自由,我們還保留了一個自由的火 種:在有關社會的起源、人類的原始權力及政府的本質等方面的哲學辯 論上,我們還可以毫無顧忌地進行探討。 在這種背景下,政治生活被理所當然地推入到文學之中。
那些深受 日常法規限制的人立即喜歡上了這種文學政治,對於那些由於社會地位 或天分所限,一直遠離抽象思辨的人來說,文學政治也成了他們的避難 所。只要是受到不平等軍役稅攤派或是貴族損害的納稅人,在聽說了人 人都天生平等這種思想後,無一不感到振奮;又聽說一切特權都應當受 到理性的譴責,無不為之雀躍。一時間,公眾的情緒持續發酵,作家成 了輿論的控制者,佔據了一個國家中本該由政黨領袖所佔有的地位,再 沒人能夠與之爭奪。
在英國,經常研究治國理論的作家與國家的統治者是混合在一起 的,統治者將新思想引進實踐,研究者藉助實踐來糾正和限定理論。而 在法國,政界幾乎分成了兩個區域,在一個區域,進行治國理民的實 踐;在另一個區域,制定抽象原則,任何政府均應以此為基礎。奇怪的 是,這兩個區域幾乎互不往來、彼此分割。在這邊,人們採取日常事務 所要求的具體措施;在那邊,人們宣揚普遍法則,卻從不考慮如何實 施。這就相當於:一些人負責領導事務,另一些人負責指導思想。
這種狀況也造成了一種分歧:現實的社會結構還是那種傳統的、混 亂的、非正規的,法律仍舊雜亂,矛盾重重,等級森嚴,負擔不平等; 在此基礎上,一個虛構的社會也開始營造起來,在這個社會裡,一切顯 得特別簡單、和諧,一切都合乎理性。 於是,普通群眾開始逐漸沉湎於虛構社會,拋棄了現實社會。他們 對現實狀況絲毫不感興趣,他們想的更多的是將來可能如何,這也就是 他們在精神上終於到達了作家們建造起來的那個理想的國度。
研究法國革命史的人應該清楚,大革命的指導思想恰巧是和那些卷 帙浩繁的評論治國的抽象著作是一樣的:即本著對一般理論,對完備的 立法體系和精確對稱的法律的相同愛好;對現存事物的同等蔑視;對理 論的同樣信任;對於政治機構中獨特、精巧、新穎的東西的同一興致; 遵照邏輯法則,依據統一方案,一舉徹底改革結構,而不在枝節上修修 補補。
這是何等令人感到害怕的景象!因為有些東西在作家身上表現出 來的會是美好的,可是如果移植到政治家身上,可能就會變成災難性的 後果,那些帶來美好著作的事物,卻很可能導致一場浩大的革命。
三、大革命後的法國,留下了中央集權的舊制度,而且比舊制度更為集權。 最後政府被拿破崙獲取,國家變成一個帝國,一個比過往更為集權專制的國家狀況,最後,拿破崙倒台,波旁王朝回來執政,國家又回到王權封建貴族體制,法國在保皇黨跟帝制之間來回擺盪爭鬥。 實在很難看出法國大革命帶來甚麼民主機制,也很難看到自由的體現。
一本書會我帶來不一樣的視角,不同的看法。 這是我從托克維爾的角度看到的大革命。 這本書也更加堅定自己追求自由的心,反專制的立場,感謝自己生在台灣。





 留言列表
留言列表